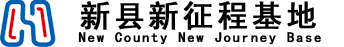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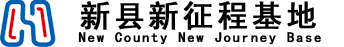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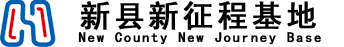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20日来到张掖市高台县,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再现了当年西路军英勇奋战、血决祁连的那段悲壮历程。习近平仔细端详,深情回顾西路军的英雄事迹。他强调,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西路军是战史上一个有过争议的问题,总体可以概括如下:我们讲西路军的征战历程,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为什么要渡河?为什么要孤军深入?为什么未能东返?为什么损失惨重?以及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图为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图为位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图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内的雕塑)
四、为什么损失惨重
一是轻敌。大家普遍认为,河西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
李先念同志晚年有段回忆:
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之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基本被我击溃。对形势估计判断错误,发生失误。古浪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感到“出人意料”(没有想到九军损失了两千多人);高台保卫战,董振堂奉命死守高台,两千八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难,对西路军领导“震动很大”。
从总体看,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我们吃大亏的一个前提条件。马家军的核心就是马步芳的青海第100师,警备第1旅、第2旅,马步青的骑兵5师,总兵力不到3万。
我们对马家军的认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并不看好它,但后来遭到失败,又把对手描述得十分强大,不仅具有兵力优势,还有装备优势,使我们陷于对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显著的优势。其武器装备较我军低劣,民团方面更谈不上训练,持长矛大刀及19世纪的毛瑟铅丸火枪。
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的领导说过:马匪作战能力不行。董振堂当初在西北军服役的时候,1928年曾在永登与马家军作过战,对方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所以他认为马家军训练水平低,作战能力不强,渡过黄河打垮马家军没有多大问题。
当时红军指挥员中发生这样的对敌人判断失误,不止董振堂一个,中央红军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1933年3月4日,马鸿逵第105旅进占光山郭家河村,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3月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74师秘密急行军60里到达郭家河,乘敌人地生疏、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进攻,以伤亡30人代价歼敌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及其下属官兵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余人落荒而逃。
这些战例都大大增强了红军面对马家军作战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但当时低估了对手,觉得可能。
中央红军也发生过低估敌人的问题。遵义会议开完,确立的战略方针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中的几位川籍将领向中央的建议,认为川军好打,作战能力不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有问题。遵义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结果土城一役吃了大亏。
所以,对敌人的低估不仅发生在西路军,中央红军照样发生。尤其五军军长董振堂长期在西北作战,对马家军是了解的。他向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建议,认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会给西路军主要领导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经离开西北多年,而这段时间内马家军也是有变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战的马家军,三日一操练,半年一会操,多数士兵把给养拿回去过生活。所以甘、青一带有“只吃粮,不当兵”之说。
说是去当兵,当什么兵啊,把粮食拿回家去了,也没什么训练,就是三天去出个操,半年去会个操,非常松散的部队。在围攻古浪作战时,马家军缺乏现代化训练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因不熟悉陆空联络技术,不懂得要布置通讯布板,被前来助战的国民党飞机炸死士兵10多名,军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军校学习的时候,马步芳也在保定军校学习。马步芳后来又在西北军干过,觉得西北军的训练非常好。董振堂他们打完仗离开西北之后,马步芳掌握军队,认真仿照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使军队的素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家军的骑兵在机动性上确实胜红军一筹。
西路军刚刚宿营做饭,马家军一见红军炊烟,急驰而至,将来不及吃的饭食挑翻倾倒后立即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给西路军造成极大困扰。过去我们习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马家军也来这一套,来得快,跑得也快,确实在战法上就让西路军十分被动。
马步芳自己编的“马家军骑兵歌”: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
这是一个我们不大看得上的对手,却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1936年11月,马家军召开武威军事会议。攻打古浪的敌指挥官、旅长马元海(此人给西路军造成了最大伤害,任第一线总指挥)在会上发言:
与共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所用兵力不多,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
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们的短处看透了,利用这一点,其兵力装备虽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红军,用他的骑兵快速截我后卫。就因为这个武威军事会议,马元海的理论深得马家军其他将领的赞赏,把他推为步骑兵全军总指挥。
马家军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在连发武器打击和炮火摧毁下,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带的部队炮兵没有问题,连发武器没有问题,所以彭德怀过了兰州往西北打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西路军的这种场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扫荡,全部消灭光。马家军这种战法在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步兵、炮兵根本无法抗衡。
但在当时红军的简陋装备之下,马家军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们出现了问题,未坚持集中兵力。
中央11月25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
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又电:
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全部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范围内,齐打齐进。
后来发生的西路军在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期间,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一次一次地吃了没有集中兵力的亏。
陈昌浩就讲:我们确实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中兵力击敌;在甘、红、古浪时集中兵力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能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高台那一战,五军的电台掌握在政委黄超手里,五军军长董振堂孤军奋战,却无法向后方转告信息。因为黄超不在高台,导致整个部队失联,援兵不及,五军受到重创,董振堂牺牲。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轻敌。
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讲的一样: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
胡绳还讲:“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当时,对方针的分歧确实发生在了高层,但是我们讲这些分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装起义,海陆丰起义、湘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赣南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共产党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是来自不同山头的武装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赣南和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红军,以鄂豫皖苏区为核心的红四方面军,以湘鄂西苏区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
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
当时,红四军内部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军必须完成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一支农民队伍怎么变成一个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于李自成、陈胜吴广、黄巢和太平天国的队伍?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落在了古田会议上。
毛泽东当时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时红四军内部朱、毛之间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学者和我们一些搞党史的人说成是毛泽东争权、揽权。毛泽东就是争,但不是为个人争,而是为党争。要通过集中统一指挥实现改造,进而才能实现胜利。
西路军的问题,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有人又说是毛泽东争权,争张国焘的军权。毛泽东争的是红军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获得胜利。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没有统一步骤和一致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胜利,不可能把我们与太平天国划分开来,与陈胜吴广划分开来。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应该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宁)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夺取宁夏。但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河,渡过黄河占领甘北,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不愿意与中央会合。他对陈昌浩说: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10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共商:
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为宜;
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不知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
毛泽东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10月28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及各军首长: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个方面军要联合起来,否则麻烦。结果话音刚落,10月29日五军过河。从今天来看,西路军作战能力原本强劲,它的整个历史也非常悲壮,但是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
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过去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说成是擅自行动。
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全战役需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过实际作战,真正获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彭德怀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
彭向中央报告:
张对打击胡敌始终动摇,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张国焘不想先打,想先到定远营获取苏联援助物资,这给当时中央的指挥号令带来重大问题。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断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西路军由此成为孤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指挥步调不统一带来的重大问题。
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电报里面几次写到“独立”“独立开展一个局面”“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还特别指出“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实质上是强调,中央来电,你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你们有专断权,关键要搞出一个独立的局面来。这就是在当时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路军的复杂指挥体制。
11月16日,西路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立即批准:
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政策路线和战略方针有伟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北、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域,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
“独立行动”“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这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独立地搞出一个局面。
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三是错判。
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
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彭德怀:
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条件较好,缺点是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都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错判之二,是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
“西安事变”以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与西北、东北军的合作,使整个西路军的处境发生重大改善。当时我们与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和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达成协议,都是要改善西路军的处境,而且几个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可见当时中央是看好西进的,认为西路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军进抵西安。东北军、西北军为保证西安的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一部分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于是中央改变西路军西进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配合东北军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革军委主席电示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仍应执行西进任务。
随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攻西安。根据形势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出现“反复拉锯”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对当时形势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判断。对东北军、西北军能不能与红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判断,对东北军控局能力的判断,等等。这一系列判断之间的拉锯,导致了后来西路军行动的来回拉锯,在倪家营子的来回拉锯。
这种拉锯有点儿像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来回地调集部队,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渡过去,一会儿渡回来。当时部队中充满了怨言,连林彪都发牢骚说,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这是部队不了解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决策就是根据敌人的布势来回地改变。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很大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几乎没有影响。
为了援助西路军,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当时对东北军抱了希望,也对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电周恩来:
与于学忠商调1师、2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希望东北军在西路军解除困境方面发挥作用。
2月24日,毛泽东再电在西安作为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毛泽东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毛泽东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毛泽东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不认的事实;说毛泽东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把西路军问题变成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指挥权力之争,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
五、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
讲到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中共党史》第一卷曾对西路军做出这样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中,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在影片《惊沙》中,高台之战、临泽之战集中体现了西路军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红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图为第一部反映红军西路军战斗历史的电影《惊沙》的海报)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中以弱击强、以劣胜优,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令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支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血脉。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
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产生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琢磨和牢记:“如果指挥员判断错了,那么就只能靠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去力挽狂澜。”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讲:“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着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这是西路军留给后人的最顽强的奋斗之音。
西路军在河西战场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汇入了历史长河,正在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远。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就像西路军高台的这座丰碑一样,永远映照着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
八十多年过去,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然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永放光芒。我们今天讲西路军问题,一方面是激情,浴血奋战、战斗到最后;另一方面要讲理性,要看到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转变的过程之中:
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必须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人不适应中国革命有可能而且一定要从分散到集中。
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过去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独立指挥自己的力量,现在要统一指挥。
三是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向统一抗战的转变。
西路军问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中央指挥机构开始对全部红军实行战略性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最为重大的转变。古田会议是一个转变,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央红军的全部领导,实现了中央苏区内的统一指挥。
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不论有无这一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这种历史性转变必然进行。没有这样的失败,转变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转变本身不可阻止。中国共产党要获得胜利,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如何夺取胜利,问题依然严重地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这注定是必须经历无数磨难、付出重大牺牲才能认识和解决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绝不是开一次两次会议、经过一次两次谈心就能完成。
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统一最终也是人的思想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很难做到。在这样一个完成思想与组织高度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眼光最远,贡献也最大。“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朝历代任何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使这支军队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这支军队的军魂也在此铸就。
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编织交错而成的。这是我们今天观察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的视野。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东方的政治舞台,西路军就是打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通道。援助地点不断地改变则是苏日之间矛盾造成的结果,而“西安事变”更是日本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苏联与日本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西路军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今天,我们看西路军问题,绝不能孤立地就红军看西路军,就河西走廊看西路军,就四方面军看西路军,越看思路越窄,越看心结越深。而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在东方政治舞台博弈的角度来观察西路军的命运。
表面上看包含了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认识差距、红军与地方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等等;从大的视野看,则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革命军队艰难痛苦的蜕变。
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关键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胸襟。一定要建设一支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坚决贯彻军政号令的队伍,才能获得胜利。国民党前参谋总长郝伯村写的《解读蒋公日记》,总结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失败时说:
国共斗争两党体制上有根本差异,共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工农群众起家,毛泽东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以内部检讨、坦白、批判形成党内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国民党看似集权,实际是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不能深入基层,不能植根于农村,导致国民党满盘皆输。
这是我们的对手对共产党为什么获得胜利的概括总结。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一定要夺取这样的胜利。
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会见当时西路军的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讲到客观原因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米宽的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缺乏同骑兵作战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他还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做不到的。”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主席最后站起来,走了几步,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桌子上,望着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广大西路军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长矛和敌人厮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一个军队胜利,绝不能仅凭拼杀的精神。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失败。
西路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从来不能淹没四方面军是我们军队中战将杰出的队伍,他们是从苦难之中拼杀出来的一批将领,很多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都来自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这样的力量。
西方著名军事学者克劳塞维茨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之源,不仅包括西路军的苦难,还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难,包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苦难: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损失5万红军,染红了湘江。
中国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蒋介石都觉得红军肯定不行了,肯定失败了,但就是不败,这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克劳塞维茨说:“一旦武德的幼芽成长成粗壮的大树,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我们当年的红军力量,就是通过一道道艰难奋战、浴血牺牲的关口形成武德,长成粗壮的大树,前仆后继地向前奋斗,最后获得全国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奠定在牺牲多少先烈的基础之上。我们达成这样的胜利,任何人的牺牲都不是白白牺牲,都成了胜利最坚实的基础。
山川地貌的巨变,历史前进的距离,是多少代人牺牲的成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定要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一代奋斗不息,最终实现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心胜3》,作者为金一南)